夏樂哈爾
那天,我跟著夏樂哈爾一起騎馬來到湖邊,草地依著湖水,水清澈見底,我看的見每一粒石子的顏色,湖水輕輕地拍打著湖岸,像母親每一口呵護的氣息。
悄悄地,目光隨著光線的路徑,緩緩抬頭。瞇著眼,我覺得自己在飛,在心裡飛。環湖的山巒似躺臥的美人,守護著賽里木湖的傳說,此時,夏樂哈爾也默默地說起哈薩克與賽里木。
這片草原,是他從小長大的環境,喝的是這裡的水,吃的是這裡養出來的羊,騎的是在這此奔馳的馬,聞的是這裡的野花,看的是這裡的日出與日落。
「以前的這裡更漂亮。」他說。
漢人來了,道路開闢了,雖然拆掉了先前蓋滿湖邊的旅舍,但湖水髒了,草地也長不出以前長及小腿的牧草了。
「我怕以後哈薩克族也和滿族一樣,消失了。
可以團結,但不能是漢化。他們不懂,我們反對是因為害怕,害怕哈薩克的傳統就要消失了。哈薩克在這裡放牧了幾百年,我們愛惜著這裡的每一分每一毫,每滴水每朵花都是我們的一部分。
但漢人來了,在清澈的湖裡撒尿,拔起美麗的野花,丟掉我們做的饢。漢人可以來,但為什麼他們不懂得珍惜呢?
看,你看那片草原,都不見了。」他說。
夏樂哈爾打著水漂,望著遠方,好似望著那昔日的牧場。
我也隨著他,想像著那樣的草原,想像著從小就在草原上的生活。
「這是我的家。」最後,他淡淡的說:
「捨不得啊,捨不得我的家。」
呼喚
當夕陽逐漸西斜,是騎馬登高的時刻。往上,再往上,我越過大牧場,爬上漸陡的山丘,穿進針葉樹林,馬兒在林間穿梭,馬蹄踩過樹枝發出咔吱咔吱的聲響,那是枝子斷裂、松果碎裂的聲音。剎那,我以為自己是愛麗絲身處夢境中,只是,眼前的小白兔不再是拿著時鐘奔跑的緊張模樣。
再上,馬兒有些喘了,我也倒在草地上休息,讓皮膚接觸這有些濕冷的青草,毛孔吸收著草地吐出的芬香。再跨過一座陡峭的小丘,夏樂哈爾拴住馬兒,我們踩著最後幾步向上的步伐,一片大雪山「唰」的一聲,清晰又穩當地,橫臥在前
「參天松如筆管直,森森動有百餘尺,萬株相倚郁蒼蒼。」邱處機曾如此形容這片山林。大雪山底是著名的果子溝,當初是由清朝林則徐來此初闢穿梭於山溝中的古道。松樹層層疊疊,密密匝匝。現今,因為公路的修建,我想已無當初如觀松林海之感,但那些仍毅力的參天古松,悄悄地送來了當時殘餘的氣息。
轉身,就是因著夕照而波光閃閃的賽里木湖。
傳說賽里木湖最早是百花盛開的草原,一對蒙古族的情人在此放牧因而相愛。但女孩在某次放牧時,遭受草原魔王的戕害,她寧死不從,拿起玉鐲擲向魔王,玉鐲落地,大地迸裂,突露深潭,姑娘縱身而入。男孩趕到,雖砍死了魔王卻因失去女孩痛不欲身,於是也跳入潭中,一對含恨而死的戀人,湧出的淚水成了賽里木湖。
自己到底也永遠成不了草原的一部分,這裡有著時間靜止的錯覺,因為靜止,好似也無法往前。我終究只能停駐旁觀,那樣的日子僅僅是生命的某種經驗,只能是一種經驗而不是本質。
這是一個沒有海的世界。世界很大,但草原上的夢想不一樣,再多的想像也填不滿它。
抑或許,它很小,只是我無從想像。
這裡的風很冷,太陽卻很大,好似永遠沒個平衡,抓不住,只是因為自己待再久,終究也只能是個過客。我記得夏樂哈爾聲音裡的失望,是那道出曾經夢想的悲傷,以及無法讀大學的難過。夏樂哈爾的世界是我一輩子都無法理解的世界,我只能聽,只能旁觀。
原來,真的有個世界,是永遠怎麼樣也走不進的世界。
到底自己是用什麼眼光、什麼身分,去看這裡的一切。在真正接觸過後,我有著無以言喻,也無從聊起的感觸。好似一個不願被分開、屈降的一體,硬生生地被這麼扯開了。
而我無以名狀地惆悵著,頻頻回顧。
我望著賽里木湖,一直望著,直到湖面上閃爍的最後一點夕陽金光消失為止。經過最後的那一段路,我用雙腳奔馳在湖邊的大草原,是昔日熟悉的冰冷溫度,縱使只有短短的五分鐘,我很開心。
本文出自:《中亞,聽見邊境的心跳》
作者:洪滋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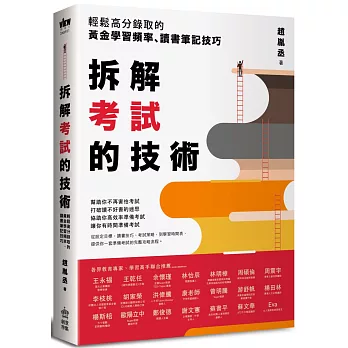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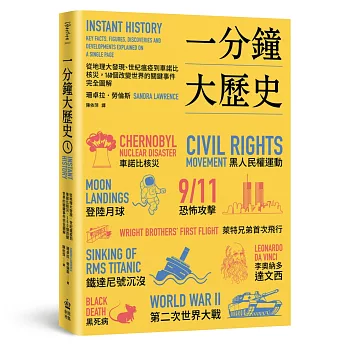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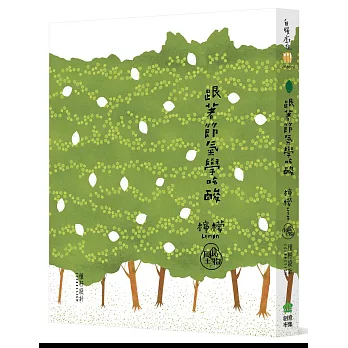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